人物简介
 李德裕
李德裕《新唐书.艺文志》着录李德裕《会昌一品集》20卷﹐又《姑臧集》5卷﹐《穷愁志》3卷﹐《杂赋》2卷。《会昌一品集》又名《李文饶文集》﹐今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刻本﹐计本集20卷﹐内皆武宗时制诰﹔别集10卷﹐则为诗赋杂文﹔外集4卷﹐即《穷愁志》﹐乃南迁后闲居论史之作。事迹见新﹑旧《唐书》本传。傅璇琮《李德裕年谱》疑《穷愁志》非李德裕作﹐至少其中掺入伪作。
生平简介
 李德裕
李德裕公元844年,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,平定泽、涟等五州。功成,加太尉赐封卫国公。
长期与李宗闵及牛僧儒为首的朋党斗争,后人称为"牛李党争",延续40年.牛李党争最早可上溯唐宪宗时文饶父吉甫与牛等的矛盾.纵观史实,文饶执政功勋卓著,威震天下;牛党执政,无所作为,国势日弱.武宗即位,信用文饶,一扫朋党,内平河北藩镇,强藩觫手;外击破回纥,威震土蕃南诏.唐室几竟中兴.宣宗即位,嫉文饶威名,初贬荆南,次贬潮州。
大中二年(公元848年)再贬崖州(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)司户,次年正月抵达。大中四年(公元850年)正月卒于贬所,终年63岁,逝后被封太尉,赠卫国公。李德裕在琼期间,著书立说,奖善嫉恶,备受海南人民敬仰,生前代表作有《会昌一品集》、 《左岸书城》、 《次柳氏旧闻》等。
人生事迹
 李德裕
李德裕李德裕,字文饶,元和宰相吉甫子也。少力于学,既冠,卓荦有大节。不喜与诸生试有司,以廕补校书郎。河东张弘靖辟为掌书记。府罢,召拜监察御史。
穆宗即位,擢翰林学士。帝为太子时,已闻吉甫名,由是顾德裕厚,凡号令大典册,皆更其手。数召见,赉奖优华。帝怠荒于政,故戚里多所请丐,挟宦人讠冋禁中语,关托大臣。德裕建言:“旧制,驸马都尉与要官禁不往来。开元中,诃督尤切,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。是等无佗材,直泄漏禁密,交通中外耳。请白事宰相者,听至中书,无辄诣第。”帝然之。再进中书舍人。未几,授御史中丞。
吉甫相宪宗,牛僧孺、李宗闵对直言策,痛诋当路,条失政。吉甫诉于帝,且泣,有司皆得罪,遂与为怨。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,李逢吉沮解其言,功未既而吉甫卒,裴度实继之。逢吉以议不合罢去,故追衔吉甫而怨度,摈德裕不得进。至是,间帝暗庸,讠木度使与元稹相怨,夺其宰相而己代之。欲引僧孺益树党,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。俄而僧孺入相,由是牛、李之憾结矣。
 李德裕
李德裕敬宗立,侈用无度,诏浙西上脂朅妆具,德裕奏:“比年旱灾,物力未完。乃三月壬子赦令,常贡之外,悉罢进献。此陛下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,雕窭之人不胜其敝也。本道素号富饶,更李锜、薛苹,皆榷酒于民,供有羡财。元和诏书停榷酤,又赦令禁诸州羡余无送使。今存者惟留使钱五十万缗,率岁经费常少十三万,军用褊急。今所须脂朅妆具,度用银二万三千两,金百三十两,物非土产,虽力营索,尚恐不逮。愿诏宰相议,何以俾臣不违诏旨,不乏军兴,不疲人,不敛怨,则前敕后诏,咸可遵承。”不报。方是时,罢进献,不阅月,而求贡使者足相接于道,故德裕推一以讽它。
又诏索盘绦缭绫千匹,复奏言:“太宗时,使至凉州,见名鹰,讽李大亮献之,大亮谏止,赐诏嘉叹。玄宗时,使者抵江南捕、翠鸟,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,即见褒纳。皇甫询织半臂、造琵琶捍拨、镂牙筩于益州,苏颋不奉诏,帝不加罪。夫、镂牙,微物也。二三臣尚以劳人损德为言,岂二祖有臣如此,今独无之?盖有位者蔽而不闻,非陛下拒不纳也。且立鹅天马,盘绦掬豹,文彩怪丽,惟乘舆当御。今广用千匹,臣所未谕。昔汉文身衣弋绨,元帝罢轻纤服,故仁德慈俭,至今称之。愿陛下师二祖容纳,远思汉家恭约,裁赐节减,则海隅苍生毕受赐矣。”优诏为停。
自元和后,天下禁毋私度僧。徐州王智兴绐言天子诞月,请筑坛度人以资福,诏可。即显募江淮间,民皆曹辈奔走,因牟撷其财以自入。德裕劾奏:“智兴为坛泗州,募愿度者,人输钱二千,则不复勘诘,普加髡落。自淮而右,户三丁男,必一男剔发,规影傜赋,所度无算。臣阅度江者日数百,苏、常齐民,十固八九,若不加禁遏,则前至诞月,江淮失丁男六十万,不为细变。”有诏徐州禁止。
时帝昏荒,数游幸,狎比群小,听朝简忽。德裕上《丹扆六箴》 ,表言:“‘心乎爱矣,遐不谓矣’,此古之贤人笃于事君者也。夫迹疏而言亲者危,地远而意忠者忤。臣窃惟念拔自先圣,遍荷宠私,不能竭忠,是负灵鉴。臣在先朝,尝献《大明赋》以讽,颇蒙嘉采。今日尽节明主,亦由是也。”其一曰《宵衣》,讽视朝希晚也;二曰《正服》,讽服御非法也;三曰《罢献》,讽敛求怪珍也;四曰《纳诲》,讽侮弃忠言也;五曰《辨邪》 ,讽任群小也;六曰《防微》,讽伪游轻出也。辞皆明直婉切。帝虽不能用其言,犹敕韦处厚谆谆作诏,厚谢其意。然为逢吉排笮,讫不内徙。斋
时亳州浮屠诡言水可愈疾,号曰“圣水”,转相流闻,南方之人,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。既行若饮,病者不敢近荤血,危老之人率多死。而水斗三十千,取者益它汲,转鬻于道,互相欺訹,往者日数十百人。德裕严勒津逻捕绝之,且言:“昔吴有圣水,宋、齐有圣火,皆本妖祥,古人所禁。请下观察使令狐楚填塞,以绝妄源。”从之。帝方惑佛老,祷福祈年,浮屠方士,并出入禁中。狂人杜景先上言,其友周息元寿数百岁,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,诏在所驰驿敦遣。德裕上疏曰:“道之高者,莫若广成、玄元;人之圣者,莫若轩辕、孔子。昔轩辕问广成子治身之要,曰:‘无视无听,抱神以静,形将自正。无劳子形,无摇子精,乃可长生。慎守其一,以处其和。故我脩身千二百岁矣,形未尝衰。’又曰:‘得吾道者上为皇,下为王。’玄元语孔子曰:‘去子之骄气与多欲、态色与淫志,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’陛下脩轩后之术,物色异人,若使广成、玄元混迹而至,告陛下之言,亦无出于此。臣虑今所得者,皆迂怪之士,使物淖冰,以小术欺聪明,如文成、五利者也。又前世天子虽好方士,未有御其药者。故汉人称黄金可成,以为饮食器则寿。高宗时刘道合、玄宗时孙甑生皆能作黄金,二祖不之服,岂非以宗庙为重乎?傥必致真隐,愿止师保和之术,慎毋及药,则九庙尉悦矣。”息元果诞谲不情,自言与张果、叶静能游。帝诏画工肖状为图以观之,终帝世无它验。文宗即位,乃逐之。
太和三年,召拜兵部侍郎。裴度荐材堪宰相,而李宗闵以中人助,先秉政,且得君,出德裕为郑滑节度使,引僧孺协力,罢度政事。二怨相济,凡德裕所善,悉逐之。于是二人权震天下,党人牢不可破矣。
逾年,徙剑南西川。蜀自南诏入寇,败杜元颖,而郭钊代之,病不能事,民失职,无聊生。德裕至,则完残奋怯,皆有条次。成都既南失姚、协,西亡维、松,由清溪下沫水而左,尽为蛮有。始,韦皋招来南诏,复巂州,倾内资结蛮好,示以战阵文法。德裕以皋启戎资盗,其策非是,养成痈疽,第未决耳。至元颖时,遇隙而发,故长驱深入,蹂剔千里,荡无孑遗。今瘢夷尚新,非痛矫革,不能刷一方耻。乃建筹边楼,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,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。其部落众寡,馈餫远迩,曲折咸具。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,凡虏之情伪尽知之。又料择伏瘴旧獠与州兵之任战者,废遣狞耄什三四,士无敢怨。又请甲人于安定,弓人河中,弩人浙西。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锐。率户二百取一人,使习战,贷勿事,缓则农,急则战,谓之“雄边子弟”。其精兵曰南燕保义、保惠、两河慕义、左右连弩;骑士曰飞星、鸷击、奇锋、流电、霆声、突骑。总十一军。筑杖义城,以制大度、青溪关之阻;作御侮城,以控荣经犄角势;作柔远城,以厄西山吐蕃;复邛崃关,徙巂州治台登,以夺蛮险。
旧制,岁抄运内粟赡黎、巂州,起嘉、眉,道阳山江,而达大度,乃分饷诸戍。常以盛夏至,地苦瘴毒,辇夫多死。德裕命转邛、雅粟,以十月为漕始,先夏而至,以佐阳山之运,馈者不涉炎月,远民乃安。蜀人多鬻女为人妾,德裕为著科约:凡十三而上,执三年劳;下者,五岁;及期则归之父母。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,以地予农。蜀先主祠旁有猱村,其民剔发若浮屠者,畜妻子自如,德裕下令禁止。蜀风大变。
于是二边浸惧,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,吐蕃维州将悉怛谋以城降。维距成都四百里,因山为固,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,地无险,走长川不三千里,直吐蕃之牙,异时戍之,以制虏入者也。德裕既得之,即发兵以守,且陈出师之利。僧孺居中沮其功,命返悉怛谋于虏,以信所盟,德裕终身以为恨。会监军使王践言入朝,盛言悉怛谋死,拒远人向化意。帝亦悔之,即以兵部尚书召,俄拜中书门下平章事,封赞皇县伯。
故事,丞郎诣宰相,须少间乃敢通,郎官非公事不敢谒。李宗闵时,往往通宾客。李听为太子太傅,招所善载酒集宗闵阁,酣醉乃去。至德裕,则喻御史:“有以事见宰相,必先白台乃听。凡罢朝,由龙尾道趋出。”遂无辄至阁者。又罢京兆筑沙堤、两街上朝卫兵。常建言:“朝廷惟邪正二途,正必去邪,邪必害正。然其辞皆若可听,愿审所取舍。不然,二者并进,虽圣贤经营,无繇成功。”俄而宗闵罢,德裕代为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始,二省符江淮大贾,使主堂厨食利,因是挟赀行天下,所至州镇为右客,富人倚以自高。德裕一切罢之。
后帝暴感风,害语言。郑注始因王守澄以药进,帝少间,又荐李训使待诏,帝欲授谏官,德裕曰:“昔诸葛亮有言:‘亲贤臣,远小人,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,远贤士,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’今训小人,顷咎恶暴天下,不宜引致左右。”帝曰:“人谁无过,当容其改。且逢吉尝言之。”对曰:“圣贤则有改过,若训天资奸邪,尚何能改?逢吉位宰相,而顾爱凶回,以累陛下,亦罪人也。”帝语王涯别与官,德裕摇手止涯,帝适见,不怿,训、注皆怨,即复召宗闵辅政,拜德裕为兴元节度使。入见帝,自陈愿留阙下,复拜兵部尚书。宗闵奏:“命已行,不可止。”更徙镇海军以代王璠。
先是太和中,漳王养母杜仲阳归浙西,有诏在所存问。时德裕被召,乃檄留后使如诏书。璠入为尚书左丞,而漳王以罪废死,因与户部侍郎李汉共谮德裕尝赂仲阳导王为不轨。帝惑其言,召王涯、李固言、路隋质之,注、璠、汉三人者语益坚,独隋言:“德裕大臣,不宜有此。”谗焰少衰。遂贬德裕为太子宾客,分司东都。复贬袁州长史,隋亦免宰相。未几,宗闵以罪斥,而注、训等乱败。帝追悟德裕以诬构逐,乃徙滁州刺史。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开成初,帝从容语宰相:“朝廷岂有遗事乎?”众皆以宋申锡对。帝俯首涕数行下,曰:“当此时,兄弟不相保,况申锡邪?有司为我褒显之。”又曰:“德裕亦申锡比也。”起为浙西观察使。后对学士禁中,黎埴顿首言:“德裕与宗闵皆逐,而独三进官。”帝曰:“彼尝进郑注,而德裕欲杀之,今当以官与何人?”埴惧而出。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:“此德裕争郑注处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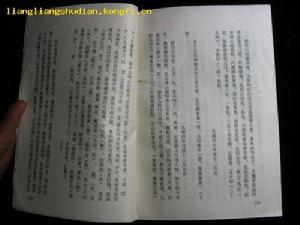 李德裕
李德裕德裕三在浙西,出入十年,迁淮南节度使,代牛僧孺。僧孺闻之,以军事付其副张鹭,即驰去。淮南府钱八十万缗,德裕奏言止四十万,为鹭用其半。僧孺诉于帝,而谏官姚合、魏谟等共劾奏德裕挟私怨沮伤僧孺,帝置章不下,诏德裕覆实。德裕上言:“诸镇更代,例杀半数以备水旱、助军费。因索王播、段文昌、崔从相授簿最具在。惟从死官下,僧孺代之,其所杀数最多。”即自劾“始至镇,失于用例,不敢妄”,遂待罪,有诏释之。
武宗立,召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既入谢,即进戒帝:“辨邪正,专委任,而后朝廷治。臣尝为先帝言之,不见用。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,小人亦谓正人为邪,何以辨之?请借物为谕,松柏之为木,孤生劲特,无所因倚。萝茑则不然,弱不能立,必附它木。故正人一心事君,无待于助。邪人必更为党,以相蔽欺。君人者以是辨之,则无惑矣。”又谓治乱系信任,引齐桓公问管仲所以害霸者,仲对琴瑟笙竽、弋猎驰骋,非害霸者;惟知人不能举,举不能任,任而又杂以小人,害霸也。“太、玄、德、宪四宗皆盛朝,其始临御,自视若尧、舜,浸久则不及初,陛下知其然乎?始一委辅相,故贤者得尽心。久则小人并进,造党与,乱视听,故上疑而不专。政去宰相则不治矣。在德宗最甚,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,所与图事者,李齐运、裴延龄、韦渠牟等,讫今谓之乱政。夫辅相有欺罔不忠,当亟免,忠而材者属任之。政无它门,天下安有不治?先帝任人,始皆回容,积纤微以至诛贬。诚使虽小过必知而改之,君臣无猜,则谗邪不干其间矣。”又言:“开元初,辅相率三考辄去,虽姚崇、宋璟不能逾。至李林甫,秉权乃十九年,遂及祸败。是知亟进罢宰相,使政在中书,诚治本也。”
帝尝疑杨嗣复、李珏顾望不忠,遣使杀之。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,即率三宰相见延英,呜咽流涕曰:“昔太宗、德宗诛大臣,未尝不悔。臣欲陛下全活之,无异时恨。使二人罪恶暴著,天下共疾之。”帝不许,德裕伏不起。帝曰:“为公等赦之。”德裕降拜升坐。帝曰:“如令谏官论争,虽千疏,我不赦。”德裕重拜。因追还使者,嗣复等乃免。
时帝数出畋游,暮夜乃还,德裕上言;“人君动法于日,故出而视朝,入而燕息。《传》曰:‘君就房有常节。’惟深察古谊,毋继以夜。侧闻五星失度,恐天以是勤勤儆戒。 《诗》曰:‘敬天之渝,不敢驰驱。’愿节田游,承天意。”寻册拜司空。
回鹘自开成时为黠戛斯所破。会昌后, 乌介可汗挟公主牙塞下,种族大饥,以弱口、重器易粟于边。退浑、党项利虏掠,因天德军使田牟上言,愿以部落兵击之。议者请可其言。德裕曰:“回鹘于国尝有功,以穷来归,未辄扰边,遽伐之,非汉宣帝待呼韩之义。不如与之食,以待其变。”陈夷行曰:“资盗粮,非计也,不如击之便。”德裕曰:“沙陀、退浑,不可恃也。夫见利则进,遇敌则走,杂虏之常态,孰肯为国家用邪?天德兵素弱,以一城与劲虏确,无不败。请诏牟无听诸戎计。”帝于是贷粟二万斛。
会嗢没斯杀赤心以降,赤心兵溃去。于是回鹘势穷,数丐羊马,欲藉兵复故地,又愿假天德城以舍公主,帝不许。乃进逼振武保大栅杷头峰,以略朔川,转战云州,刺史张献节婴城不出。回鹘乃大掠,党项、退浑皆保险莫敢拒。帝益知向不许田牟用二部兵之效,乃复问以计,德裕曰:“杷头峰北皆大碛,利用骑,不可以步当之。今乌介所恃,公主尔,得健将出奇夺还之,王师急击,彼必走。今锐将无易石雄者,请以籓浑劲卒与汉兵衔枚夜击之,势必得。”帝即以方略授刘沔,令雄邀击可汗于杀胡山,败之,迎公主还,回鹘遂败。进位司徒。
黠戛斯遣使来,且言攻取安西、北庭,帝欲从黠戛斯求其地,德裕曰:“不可。安西距京师七千里,北庭五千里。异时繇河西、陇右抵玉门关,皆我郡县,往往有兵,故能缓急调发。自河、陇入吐蕃,则道出回鹘。回鹘今破灭,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?假令安西可得,即复置都护,以万人往戍,何所兴发,何道馈輓?彼天德、振武于京师近,力犹苦不足,况七千里安西哉?臣以为纵得之,无用也。昔汉魏相请罢田车师,贾捐之请弃珠崖,近狄仁杰亦请弃四镇及安东,皆不愿贪外以耗内。此三臣者,当全盛时,尚欲弃割以肥中国,况久没甚远之地乎?是持实费,市虚事,灭一回鹘,而又生之。”帝乃止。
泽潞刘从谏死,其从子稹擅留事,以邀节度,德裕曰:“泽潞内地,非河朔比,昔皆儒术大臣守之。李抱真始建昭义军,最有功,德宗尚不许其子继。及刘悟死,敬宗方怠于政,遂以符节付从谏。太和时,擅兵长子,阴连训、注,外托效忠,请除君侧。及有狗马疾,谢医拒使,便以兵属稹。舍而不讨,无以示四方。”帝曰:“可胜乎?”对曰:“河朔,稹所恃以脣齿也。如令魏、镇不与,则破矣。夫三镇世嗣,列圣许之。请使近臣明告:‘以泽潞命帅,不得视三镇,今朕欲诛稹,其各以兵会。’”帝然之。乃以李回持节谕王元逵、何弘敬,皆听命。始议用兵,中外交章固争,皆曰:“悟功高,不可绝其嗣。又从谏畜兵十万,粟支十年,未可以破也。”它宰相亦弇婀趋和,德裕独曰:“诸葛亮言曹操善为兵,犹五攻昌霸,三越漅,况其下哉?然赢缩胜负,兵家之常,惟陛下圣策先定,不以小利钝为浮议所摇,则有功矣。有如不利,臣请以死塞责!”帝忿然曰:“为我语于朝,有沮吾军议者,先诛之!”群论遂息。元逵兵已出,而弘敬逗留持两端。德裕建遣王宰以陈、许精甲,假道于魏以伐磁。弘敬闻,遽勒兵请自涉漳取磁、潞。
会横水戍兵叛,入太原,逐其帅李石,奉裨将杨弁主留事。方是时,稹未下,朝廷益为忧。议者颇言兵皆可罢。帝遣中人马元实如太原,侦其变。弁厚贿中人,帐饮三日。还,谬曰:“弁兵多,属明光甲者十五里。”德裕诘曰:“李石以太原无兵,故调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,弁因以乱,渠能列卒如此多邪?”则曰:“晋人勇,皆兵也,募而得之。”德裕曰:“募士当以财,李石以人欠一缣,故兵乱,石无以索之,弁何得邪?太原一铠一戟,举送行营,安致十五里明光乎?”使者语塞。德裕即奏:“弁贱伍,不可赦。如力不足,请舍稹而诛弁。”遽趣王逢起榆社军,诏元逵趋土门,会太原。河东监军吕义忠闻,即日召榆社卒入斩弁,献首京师。
德裕每疾贞元、太和间有所讨伐,诸道兵出境,即仰给度支,多迁延以困国力。或与贼约,令懈守备,得一县一屯以报天子,故师无大功。因请敕诸将,令直取州,勿攻县。故元逵等下邢、洺、磁,而稹气索矣。俄而高文端归命,称稹粮乏,皆女子挼穟哺兵。未几,郭谊持稹首降。帝问:“何以处谊?”德裕曰:“稹竖子,安知反?职谊为之。今三州已降,而稹穷蹙,又贩其族以邀富贵,不诛,后无以惩恶。”帝曰:“朕意亦尔。”因诏石雄入潞,尽取谊等及尝为稹用者,悉诛之。策功拜太尉,进封赵国公。德裕固让,言:“唐兴,太尉惟七人,尚父子仪乃不敢拜。近王智兴、李载义皆超拜保、傅,盖重惜此官。裴度为司徒十年,亦不迁,臣愿守旧秩足矣。”帝曰:“吾恨无官酬公,毋固辞。”德裕又陈:“先臣封于赵,冢孙宽中始生,字曰三赵,意将传嫡,不及支庶。臣前益封,已改中山。臣先世皆尝居汲,愿得封卫。”从之,遂改卫国公。
帝尝从容谓宰相曰:“有人称孔子其徒三千亦为党,信乎?”德裕曰:“昔刘向云:‘孔子与颜回、子贡更相称誉,不为朋党;禹、稷与皋陶转相汲引,不为比周。无邪心也。’臣尝以共、鮌、驩兜与舜、禹杂处尧朝,共工、驩兜则为党,舜、禹不为党。小人相与比周,迭为掩蔽也。贤人君子不然,忠于国则同心,闻于义则同志,退而各行其己,不可交以私。赵宣子、随会继而纳谏,司马侯、叔向比以事君,不为党也。公孙弘每与汲黯请间,黯先发之,弘推其后,武帝所言皆听。黯、弘虽并进,然廷诘齐人少情,讥其布被为诈,则先发后继,不为党也。太宗与房玄龄图事,则曰非杜如晦莫能筹之。及如晦在焉,亦推玄龄之策。则同心图国,不为党也。汉硃博、陈咸相为腹心,背公死党。周福、房植各以其党相倾,议论相轧,故朋党始于甘陵二部。及甚也,谓之钩党,继受诛夷。以王制言之,非不幸也。周之衰,列国公子有信陵、平原、孟尝、春申,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,亦各有客三千,务以谲诈势利相高;仲尼之徒,唯行仁义。今议者欲以比之,罔矣。臣未知所谓党者,为国乎?为身乎?诚为国邪,随会、叔向、汲黯、房、杜之道可行,不必党也。今所谓党者,诬善蔽忠,附下罔上,车马驰驱,以趋权势,昼夜合谋,美官要选,悉引其党为之,否则抑压以退。仲尼之徒,有是乎?陛下以是察之,则奸伪见矣。”
时韦弘质建言:“宰相不可兼治钱谷。”德裕奏言:“管仲明于治国,其语曰:‘国之重器,莫重于令。令重君尊,君尊国安。治人之本,莫要于令。’故曰‘亏令者死,益令者死,不行令者死,留令者死,不从令者死。五者无赦。’又曰:‘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,是主威下系于人也。’太和后,风俗浸敝,令出于上,非之在下。此敝不止,无以治国。匡衡曰:‘大臣者,国家股肱,万姓所瞻仰,明主所慎择也。’ 《传》曰:‘下轻其上爵,贱人图柄臣,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。’今弘质为人所教而言,是图柄臣者也。且萧望之,汉名儒,为御史大夫,奏云:‘岁首,日月少光,咎在臣等。’宣帝以望之意轻丞相,下有司诘问。贞观中,监察御史陈师合上言:‘人之思虑有限,一人不可总数职。’太宗曰:‘此欲离间我君臣。’斥之岭外。臣谓宰相有奸谋隐慝,则人人皆得上论。至于制置职业,人主之柄,非小人所得干。古者朝廷之士,各守官业,思不出位。弘质贱臣,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!是轻宰相。陛下照其邪计,从党人中来,当遏绝之。”德裕大意,欲朝廷尊,臣下肃,而政出宰相,深疾朋党,故感愤切言之。
又尝谓:“省事不如省官,省官不如省吏,能简冗官,诚治本也。”乃请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,衣冠去者皆怨。时天下已平,数上疏乞骸骨,而星家言荧惑犯上相,又恳丐去位,皆不许。当国凡六年,方用兵时,决策制胜,它相无与,故威名独重于时。宣宗即位,德裕奉册太极殿。帝退谓左右曰:“向行事近我者,非太尉邪?每顾我,毛发为森竖。”翌日,罢为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荆南节度使。俄徙东都留守。白敏中、令狐綯、崔铉皆素仇,大中元年,使党人李咸斥德裕阴事。故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,再贬潮州司马。明年,又导吴汝纳讼李绅杀吴湘事,而大理卿卢言、刑部侍郎马植、御史中丞魏扶言:“绅杀无罪,德裕徇成其冤,至为黜御史,罔上不道。”乃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。明年,卒,年六十三。德裕既没,见梦令狐綯曰:“公幸哀我,使得归葬。”綯语其子滈,滈曰:“执政皆共憾,可乎?”既夕,又梦,綯惧曰:“卫公精爽可畏,不言,祸将及。”白于帝,得以丧还。
德裕性孤峭,明辩有风采,善为文章。虽至大位,犹不去书。其谋议援古为质,衮衮可喜。常以经纶天下自为,武宗知而能任之,言从计行,是时王室几中兴。
先是,韩全义败于蔡,杜叔良败于深,皆监军宦人制其权,将不得专进退,诏书一日三四下,宰相不豫。又诸道锐兵票士,皆监军取以自随,每督战,乘高建旗自表,师小不胜,辄卷旗去,大兵随以北。繇是王师所向多负。至讨回鹘、泽潞,德裕建请诏书付宰司乃下,监军不得干军要,率兵百人取一以为卫。自是,号令明壹,将乃有功。
元和后数用兵,宰相不休沐,或继火,乃得罢。德裕在位,虽遽书警奏,皆从容裁决,率午漏下还第,休沐辄如令,沛然若无事时。其处报机急,帝一切令德裕作诏,德裕数辞,帝曰:“学士不能尽吾意。”伐刘稹也,诏王元逵、何弘敬曰:“勿为子孙之谋,存辅车之势。”元逵等情得,皆震恐思效。已而三州降,贼遂平。帝每称魏博功,则顾德裕道诏语,咨其切于事而能伐谋也。三镇每奏事,德裕引使者戒敕为忠义,指意丁宁,使归各为其帅道之,故河朔畏威不敢慢。后除浮屠法,僧亡命多趣幽州,德裕召邸吏戒曰:“为我谢张仲武,刘从谏招纳亡命,今视之何益?”仲武惧,以刀授居庸关吏曰:“僧敢入者,斩!”
帝既数讨叛有功,德裕虑忲于武,不可戢,即奏言:“曹操破袁绍于官渡,不追奔,自谓所获已多,恐伤威重。养由基古善射者,柳叶虽百步必中,观者曰:‘不如少息,若弓拨矢钩,前功皆弃。’陛下征伐无不得所欲,愿以兵为戒,乃可保成功。”帝嘉纳其言。方士赵归真以术进,德裕谏曰:“是尝敬宗时以诡妄出入禁中,人皆不愿至陛下前。”帝曰:“归真我自识,顾无大过,召与语养生术尔。”对曰:“小人于利,若蛾赴烛。向见归真之门,车辙满矣。”帝不听。于是挟术诡时者进,帝志衰焉。
所居安邑里第,有院号“起草”,亭曰“精思”,每计大事,则处其中,虽左右侍御不得豫。不喜饮酒,后房无声色娱。生平所论著多行于世云。
子烨,仕汴宋幕府,贬象州立山尉。懿宗时,以赦令徙郴州。余子皆从死贬所。烨子延古,乾符中,为集贤校理,擢累司勋员外郎,还居平泉。昭宗东迁,坐不朝谒,贬卫尉主簿。
德裕之斥,中书舍人崔嘏,字乾锡,谊士也。坐书制不深切,贬端州刺史。嘏举进士,复以制策历刑州刺史。刘稹叛,使其党裴问戍于州,嘏说使听命,改考功郎中,时皆谓遴赏。至是,作诏不肯巧傅以罪。吴汝纳之狱,朝廷公卿无为辨者,惟淮南府佐魏铏就逮,吏使诬引德裕,虽痛楚掠,终不从,竟贬死岭外。又丁柔立者,德裕当国时,或荐其直清可任谏争官,不果用。大中初,为左拾遗。既德裕被放,柔立内愍伤之,为上书直其冤,坐阿附,贬南阳尉。
懿宗时,诏追复德裕太子少保、卫国公,赠尚书左仆射,距其没十年。
赞曰:汉刘向论朋党,其言明切,可为流涕,而主不悟,卒陷亡辜。德裕复援向言,指质邪正,再被逐,终婴大祸。嗟乎!朋党之兴也,殆哉!根夫主威夺者下陵,听弗明者贤不肖两进,进必务胜,而后人人引所私,以所私乘狐疑不断之隙;是引桀、跖、孔、颜相哄于前,而以众寡为胜负矣。欲国不亡,得乎?身为名宰相,不能损所憎,显挤以仇,使比周势成,根株牵连,贤智播奔,而王室亦衰,宁明有未哲欤?不然,功烈光明,佐武中兴,与姚、宋等矣。
诗词鉴赏
 李德裕
李德裕内官传诏问戎机,载笔金銮夜始归。万户千门皆寂寂,月中清露点朝衣。
李德裕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名相,为政六年,内制宦官,外平幽燕,定回鹘,平泽潞,有重大政治建树,曾被李商隐誉为“万古之良相”。在唐朝那个诗的时代,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。这首《长安秋夜》颇具特色,它如同一则宰辅日记,反映着他日理万机的从政生活中的一个片断。
中晚唐时,强藩割据,天下纷扰。李德裕坚决主张讨伐藩镇,为武宗所信用,官拜太尉,总理戎机。“内官传诏问戎机”,表面看不过从容叙事。但读来却感觉到一种非凡的襟抱、气概。因为这经历,这口气,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。大厦之将倾,全仗栋梁的扶持,关系非轻。一“传”一“问”,反映出皇帝的殷切期望和高度信任,也间接透示出人物的身份。作为首辅大臣,肩负重任,不免特别操劳,忘食废寝更是在所难免。“载笔金銮夜始归”,一个“始”字,感慨系之。句中特意提到的“笔”,那决不是一般的“管城子”,它草就的每一笔都将举足轻重。“载笔”云云,口气是亲切的。写到“金銮”,这决非对显达的夸耀,而是流露出一种“居庙堂之高”者重大的责任感。
在朝堂上,决策终于拟定,他如释重负,退朝回马。当来到首都的大道上,已夜深人定,偌大长安城,坊里寂然无声,人们都沉入了梦乡。月色撒在长安道上,更给一片和平静谧的境界增添了诗意。面对“万户千门皆寂寂”,他也许感到一阵轻快;同时又未尝不意识到这和平景象要靠政治统一、社会安定来维持。骑在马上,心关“万户千门”。一方面是万家“皆寂寂”(显言);一方面则是一己之不眠(隐言),对照之中,间接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博大情怀。
秋夜,是下露的时候了。他若是从皇城回到宅邸所在的安邑坊,那是有一段路程的。他感到了凉意;不知什么时候朝服上已经缀上亮晶晶的露珠了。这个“露点朝衣”的细节非常生动,大概这也是纪实吧,但写来意境优美、境界高远。李煜词云:“归时休放烛花红,待踏马蹄清夜月”(《玉楼春》),多么善于享乐啊!虽然也写月夜归马,也很美,但境界则较卑。这一方面是严肃作息,那一方面却是风流逍遥,情操迥别,就造成彼此诗词境界的差异。露就是露,偏写作“月中清露”,这想象是浪漫的,理想化的。“月中清露”,特点在高洁,而这正是诗人情操的象征。那一品“朝衣”,再一次提醒他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。他那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尊自豪感跃然纸上。此结可谓词美、境美、情美,为诗中人物点上了一抹“高光”。
谪岭南道中作
岭水争分路转迷,桄榔椰叶暗蛮溪。愁冲毒雾逢蛇草,畏落沙虫避燕泥。五月畲田收火米,三更津吏报潮鸡。不堪肠断思乡处,红槿花中越鸟啼。
这首七言律诗,是李德裕在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贬岭南时所作。诗的首联描写在贬谪途中所见的岭南风光,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。第一句写山水,岭南重峦叠嶂,山溪水流湍急,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。再加上山路盘旋,行人难辨东西而迷路。这里用一“争”字,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状得更加生动,而且也点出了“路转迷”的原因,似乎道路纡回,使人迷失方向是“岭水”故意“争分”造成的。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,但又是实感,所以诗句倍添情致。第二句紧接上句进一步描写山间景色,桄榔、椰树布满千山万壑,层林叠翠,郁郁葱葱。用一“暗”字,突出桄榔、椰树等常绿乔木的茂密,遮天蔽日,连溪流都为之阴暗。这一联选取岭南最具特色的山水林木落笔,显示出浓郁的南国风光。
颔联宕开一笔,写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情况:害怕遇到毒雾,碰着蛇草;更担心那能使中毒致死的沙虫,连看见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。这样细致的心理状态的刻画,有力地衬托了岭南地区的荒僻险恶。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,这种衬托的手法,比连续的铺陈展叙、正面描绘显得更有变化,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。清人沈德潜认为这一联“语双关”,和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的《岭南江行》一诗中的“射工巧伺游人影,飓母偏惊旅客船”一样,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,诗中的毒雾、蛇草、沙虫等等都有所喻指。这样理解也不无道理。
颈联转向南方风物的具体描写,在写景中透露出一种十分惊奇的异乡之感。五月间岭南已经在收获稻米,潮汛到来的时候,三更时分鸡就会叫,津吏也就把这消息通知旅行的人,这一切和北方是多么不同啊!这两句为尾联抒发被谪贬瘴疠之地的思乡之情作铺垫。
尾联是在作者惊叹岭南环境艰险,物产风俗大异于秦中之后,引起了身居异地的怀乡之情,更加上听到在鲜艳的红槿花枝上越鸟啼叫,进而想到飞鸟都不忘本,依恋故土,何况有情之人!如今自己迁谪远荒,前途茫茫,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,思念家园,情不能己,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。这当中也深含着被排挤打击、非罪谪贬的愤懑。最后一句暗用《古诗十九首·行行重行行》中“越鸟巢南枝”句意,十分贴切而又意味深长。此联为这首抒情诗的结穴之处,所表达的感情异常深挚动人。
全诗写景抒情相互交替,景中寓情,情中有景,显得灵活多变而不呆板滞涩。
登崖州城作
独上高楼望帝京,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,百匝千遭绕郡城。
李德裕是杰出的政治家,武宗李炎朝任宰相,在短短的六年执政生涯中,外攘回纥,内平泽潞,扭转了长期以来唐王朝积弱不振的混乱局面。可惜宣宗李忱继位之后,政局发生变化,白敏中、令狐绹当国,一反会昌时李德裕所推行的政令。他们排除异己,嫉贤害能,无所不用其极;而李德裕则更成为与他们势不两立的打击、陷害的主要对象。其初外出为荆南节度使;不久,改为东都留守;接着左迁太子少保,分司东都;再贬潮州司马;最后,终于将他贬逐到海南,贬为崖州司户参军。这诗便是在崖州时所作。这首诗,同柳宗元的《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》颇有相似之处: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绝句,作者都是被贬谪失意之人,同样以山作为描写的背景。然而,它们所反映的诗人的心情却不同,表现手法及其意境、风格也迥然不同。
作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,即使处于炎海穷边之地,他那眷恋故国之情,仍然锲而不舍。王谠《唐语林》卷七云:“李卫公在珠崖郡,北亭谓之望阙亭。公每登临,未尝不北睇悲哽。题诗云⋯⋯”他登临北望,主要不是为了怀念乡土,而是出于政治的向往与感伤。“独上高楼望帝京”,诗一开头,这种心情便昭然若揭;因而全诗所抒之情,和柳诗之“望故乡”是有所区别的。“鸟飞犹是半年程”,极言去京遥遥。这种艺术上的夸张,其中含有浓厚的抒情因素。人哪能象鸟那样自由地快速飞翔呢?然而即便是鸟,也要半年才能飞到。这里,深深透露了依恋君国之情,和屈原在《哀郢》里说的“哀故都之日远”,同一含意。
再说,虽然同在迁谪之中,李德裕的处境和柳宗元也是不相同的。
 李德裕
李德裕柳宗元被贬在柳州,毕竟还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,只不过因为他曾经是王叔文的党羽,不被朝廷重用而已。他思归不得,但北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;否则他就不会乞援于“京华亲故”了。而李德裕在被迁崖州,则是白敏中、令狐绹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。在残酷无情的派系斗争中,他是失败一方的首领。此时,他已落入政敌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。历史的经验,现实的遭遇,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然会贬死在这南荒之地,断无生还之理。沉重的阴影压在他的心头,于是在登临望山时,其着眼点便放在山的重叠阻深上。“青山似欲留人住,百匝千遭绕郡城。”这“百匝千遭”的绕郡群山,不正成为四面环伺、重重包围的敌对势力的象征吗?人到极端困难、极端危险的时刻,由于一切希望已经断绝,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幸,思想上都有了准备,心情往往反而会平静下来。不诅咒这可恶的穷山僻岭,不说人被山所阻隔,却说“山欲留人”,正是“事到艰难意转平”的变态心理的折射。
诗中只说“望帝京”,只说这“望帝京”的“高楼”远在群山环绕的天涯海角,通篇到底,并没有抒写政治的愤慨,迁谪的哀愁,语气显得悠游不迫,舒缓宁静。然而正是在这悠游不迫、舒缓宁静的语气中,包孕着深沉的忧虑与感伤。情调悲怆沉郁。
